【时尚芭莎网讯】时尚芭莎
尽管2025刚开头,但今年的“年度最好哭”似乎已被提前预定——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。这部由IU和朴宝剑,以及诸多韩剧老戏骨主演的口碑新剧,从开播到上周完结。不仅打破烂尾诅咒,反而彻底坐实成了,与《请回答1988》《父母爱情》等家庭神剧同级别功力的“催泪瓦斯”。但不知道大家有没察觉?和同类型佳作相比,《苦尽柑来》实则又进了一步。它是一部少见的女性家庭剧。一个母系视角下的家庭叙事成功样本。
#
以母系为中心的
家族叙事
以往的家庭题材,最难挣脱的正是传统家庭结构的叙事惯性。对父辈的塑造,父子父女间的传承、情感、创伤,始终是家庭故事的叙事轴心。一方面这确实是对现实的普遍写照,在过去几代甚至现在的家庭里,父亲的存在感和影响力,无论是好是歹,总是不可忽视。也因此,即便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塑造母亲的亮色之作,母辈故事往往也被归入辅助线或“情感陪衬”的位置。她们,仍旧依附于父辈叙事的主轴。
今年的《苦尽柑来》,新鲜就新鲜在,它拍出了一种真正以母系为中心的家族叙事。当然,这个母系并不是说,这部剧呈现了一个标准的母系社会,或者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女儿国。而是女主爱纯的母亲全光礼,爱纯本人,还有爱纯女儿梁金明,这三代女性,哪怕是异姓,却真正活在同一个家族语境里。在这个家庭里,确立的是母辈的“权威”,传承的是母辈的精神力。
一种蛮新鲜的观感,在《苦尽柑来》里,你会发现,父辈角色的“存在感”空前的浅淡。较之以往,他们的形象,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差,而是,变得“不重要”了。就像女主爱纯,自小丧父,但没有父亲从不是她的创伤来源。爱纯的人生里,只有对母亲的执着。就像光礼去世后,爱纯对母亲的想念没有因为时间消减,反而随着人生体验的积累而愈加强烈。
在爱纯的人生叙事里,和父亲的关系不再具备“绝对必要性”,“父爱执念”根本不是她的命题。爱纯身上最显性的父系身份标识是她的姓氏。但在爱纯从小长大的济州岛,乡亲四邻却并不通过姓氏识别她。
在济州岛,爱纯在人群里最明确的身份,最受到众人认可和关照的身份,是“母亲的女儿”,是全光礼的女儿。(她是光礼的女儿)再比如爱纯的女儿金明。《苦尽柑来》的明线故事,是吴爱纯与梁宽植这对夫妻在济州岛经历人生的四季轮转。所以比起母亲爱纯,金明自小就活在一个父母在场的有爱家庭里。但就像爱纯为了不让小金明落入辛苦的“海女”命运,在梁家掀桌表态后。宽植拉着爱纯和女儿,彻底离开那个在文化上他们并不认同的传统家庭,在爱纯母亲全光礼的旧居,重新建立自己的小家。
这个小家,延续的不是梁家秉持的传统性别规训,是爱纯从母亲全光礼处继承来的精神力和人生哲学。而梁宽植,在人生和家庭规划,儿女成长的期待上,自始至终,都是爱纯理念的认可者和辅助者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他要做“第一先生”。做帮助爱纯掀桌子的人。
金明,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作为共同伙伴,一起守护爱纯家母辈精神的家庭里长大的。《苦尽柑来》的母系家庭底色,恰恰在此。不是所谓“父亲”“丈夫”客观意义上的不在场。而是在家庭叙事中,母辈角色恢复了强存在感和影响力。
再不像经典电影《令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里,松子视角下的家庭。父爱居于神圣和权威地位,母亲在父亲精神力主导的家里,连面貌自始至终都是模糊。松子的讨好人格,强迫症般和妹妹“争宠”的心理,根源都是对父爱的执念。因为没被父亲看见过,所以一辈子都渴望在父亲的目光里确认自己。
而在《苦尽柑来》里,无论爱纯还是金明,在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,不约而同都先看向母亲。如果再像个傻瓜一样过日子。如果不好好爱自己,我妈妈会哭。
对会让母亲流泪的选择,慎之又慎。被母亲认可的野心不需要羞耻。在被命运玩弄到,真的好想好想放弃的时候,会在梦见母亲后,重新振作。作为女儿的爱纯和金明,她们回应的是母亲的期待,继承的是母辈精神,人生哲学更受母系智慧滋养。
而,爱纯家族叙事其实极具“母系气质”的另一重要体现在于——你会发现,主角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,无论母女、父女还是夫妻,其关系质地都更接近于伙伴关系,而非统治关系。伙伴关系,恰恰是母系文化里,人与人关系的主要特征。
剧里有个颇具对照性的对比。在爱纯的父亲家,即家庭结构和文化都更传统的吴家。爱纯的叔叔作为家里话语权最大的男性家长,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,他的儿子钟九是长孙。
因为是长孙,再愚笨,也比爱纯有上学的优先权。因为是长孙,赌博欠了债,全家自老到小都有义务给他擦屁股。因为是长孙,是家人死后祭拜送终的人。
当爱纯叔叔在家中建立权威的方式,是借由家人的某种“死亡恐惧”来达成威慑。本质是掌控逻辑。爱纯妈妈的母系权威,却建立在她身为生命的创造者,那种近乎天赋般的对生命的照料与爱上。光礼和爱纯的母女故事线里,有一段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情节。童年时期的爱纯,在某年父亲的忌日,因为追一只蜻蜓,消失在小伙伴的眼前。知道始末的大人以为是她淘气去哪玩了,只有母亲光礼,被一种莫名的感觉牵引,匆匆翻了一整座山,千钧一发之际,拦住了被拐卖犯设计,差一点就被带上陌生车辆的小爱纯。
光礼感慨可能是祭祀日爱纯父亲在天上保佑。但是,救了爱纯的是玄学吗?救了爱纯的,是光礼。是她身为照料者的强大直觉,是一种真正的母系天赋。母系叙事,从不是单纯的性别权力的倒转。在《苦尽柑来》里,它成了一次次对女性独特精神气质与情感天赋的看见与正名。
就像剧里全光礼所属的济州岛海女社群,是一个真实的具备母系社会特征的群体。这个群体内部最大的特征,不是明确森严的等级划分与权力统治。而是海女们在长期互助劳动的工作形式里所形成的那种,身为命运共同体,坚定地互相托举与集体养育的意识。所以她们会在光礼病情严重到危及生命时,劝她停止工作。在光礼去世后,用绑着红丝带的渔网,共同帮扶光礼的孩子爱纯。慷慨而乐生的济州岛海女文化。正是海女出身的全光礼,被海女们集体养育过的乐纯,以及下一代的金明,三代女性的母系家族叙事上,最初一抹底色。
#
母女关系,
是生命的延续和扩容
这就是为什么,当我们谈及女性魅力时,总是特别偏爱一个词,叫作生命力。因为“乐生”,就是母系智慧的底层逻辑。虽然在逼仄得近乎绞杀的处境里,母辈的生命力,常被勒得变形,有时甚至呈现出某种令女儿们难以理解的畸态,但底色其实是从不停止向着有光的方向钻行,为自己,或者是下一代“挣出一条生路”。
结构的乌云难以遮蔽个体炽热的体温。《苦尽柑来》三代女性,都有这种生命的热劲,在无言地传承。爱纯的妈妈,也就是金明的姥姥光礼,在生命力的表达上,尤其炽热、尤其外显。她身上总有一股子愤怒的生劲。
性格刚硬的光礼,前夫死得早,被婆家责怪“克死”了丈夫。再婚对象性格虽然省事,却是个十足十的软饭男。光礼要靠着做拿命挣钱的古老职业“海女”,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。她的生活姿态,就是一边骂骂咧咧,一边撸起袖子咬牙干。光礼从不自欺欺人,她清晰地认知到女性命运的不公,认知到结构的重压。但她强就强在,看清生活的真相,并不影响她对生活的高执行。明明背负着那样辛苦的命运,对世界可以说怀揣着的是愤恨的光礼,却依然想着生。想要活着,多活几年,活到六十岁七十岁。光礼的愤怒不是一种玉石俱焚的死本能,而是生机的彰显。是当生命力撞到环境壁垒时,不愿就此罢休的显证。是一种因为不甘心,拼命挣扎到最后一刻的强执行哲学。生活再苦,从不躺平,用力折腾到最后一刻,才叫体验生命。
在这种“乐生”的生存姿态里,就会派生出母系智慧的另一种特征。那就是“务实”。当话语权主要落在最直接承担生育、哺育责任的女性身上时,整个家族叙事就会更聚焦在“把日子过下去”的具体技艺,还有实际的日常细节上。你会发现,在那些由女性长辈有更大影响力的家庭里,家族文化的质地,往往不依赖宏大的理念或权威的训诫,而更注重真实的体验。每一个“她式”家庭,往往都有一个独属于她们的日常意象。就像那令爱纯又爱又恨的笨鲍鱼。一个100韩元的笨鲍鱼,夺取了爱纯和妈妈的相处时间。可是母女之间最动人的互相珍惜,又凝结在光礼脱口而出的那句,“你吃值1000韩元”。也写进了爱纯那首讨伐鲍鱼的诗中——我要每天花100元,向笨鲍鱼买下妈妈的时间。
在母系叙事中,家族记忆的传承,从不依赖空洞话语和理念,比如“家训”式的权威说教。更多的,是通过日常照料的渗透,通过一套温柔有力的生活仪式,构成一套情感性的秩序,真正地去滋养每个家庭成员。
就比如《海街日记》里的梅子酒,《海街日记》的家庭,是一个由同父异母的姐妹们构成的全女家庭。姥姥留下的酿酒传统,被一家之主大姐,一丝不苟地年年延续着。当异母妹妹铃被接纳进这个家,姐姐们并不是通过漂亮话,让她感受到归属,而是让她在家里的梅子酒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口味。因为不能饮酒,大姐特地为铃酿了无酒精版的梅子酒,从那一刻起,铃的名字,便写进了这个家的味觉谱系里。
这正是母系家庭智慧最动人的部分。关爱不是宣言,不是说教。而是一种无声却精准的托举。从不说“我为你好”。而是默默把你的那一份,预留好。
还记得光礼那场精彩的“黄鱼夺女战”吗?爸爸去世后,小爱纯有段时间是在父亲家生活,却被叔叔刻薄连吃黄鱼的资格都被剥夺。感受到女儿对自己的眷恋,又知道女儿被轻待,光礼不语,只是闷声冲进叔叔家,把一袋黄鱼甩到他脸上,呛他:“不是想靠黄鱼发财吗?”发了一阵拳拳到肉的疯,然后毫不犹豫,把女儿带走。
你看,母系的关怀,就是这么精准周全,没有滔滔不绝的老生常谈,只有沉默有力的行动。那袋黄鱼,不只是一场爽感反击,更是稳稳托住了爱纯寄人篱下、差点出现裂痕的配得感。
而光礼的托举,不只发生在她还在的时候,更贯穿了爱纯整个人生。多年后,爱纯和自己小尾巴宽植结婚。婆家百般刁难,她不被看见,连带女儿金明也不被尊重。宽植不忍,拉着爱纯搬出家门,自立门户。为了生计,他去做渔民,船长却不巧是曾与爱纯有过节的相亲对象。相亲男百般刁难他,把对爱纯的旧怨撒在她爱的人身上。爱纯得知后,当即冲到码头,踢了相亲男两脚,像当时宽植拉着她离开婆家一样,拉着宽植转身就走。但这一脚,守住了尊严,却也踢碎了生路——因为相亲男的哥哥,是当地渔业合作社的社长。宽植彻底找不到工作,年轻早婚的夫妇,在那个资源短缺的时代环境,两人一度吃不起饭。没想到这个节骨眼,已经离开的母亲,仍有办法兜住自己年轻的女儿。
原来,光礼临终前,曾偷偷去找爱纯的奶奶,半恳求、半威胁地留下话:“以后她最难的时候,请你像帮儿子一样帮她一次,就当我们两清。”也许是出于对夭折儿子的愧疚;也许是对这位早逝儿媳最后的敬意;也许是对“长孙最大”文化下被忽视的孙女的一丝怜惜;抑或是出于私房钱迟早被长孙败光,不如拿来救急的理性判断;更可能是一个同在结构中身不由己的老妇人,对另一个辛苦女人的深切共情。也或许,这一切情绪都有。最终,奶奶还是拿出私房钱,替爱纯家买下了一艘打鱼的船。为爱纯几乎走投无路的小家,打下一次重启的锚点。
这样的情节,也让人想起3月正在上映的电影《还有明天》里的女主迪莉娅。表面上,她只是个不敢反抗的家庭主妇。但却能在丈夫严密监视下,偷偷为女儿攒下一笔学费;在察觉女儿即将步入一段有毒的婚姻时,她悄悄炸掉对方家开的酒吧,一脚踩停这场命运列车。看似温顺,在实际事情上,执行起来绝不马虎。她的爱,从不张扬,但不缺席。不是口号式的呐喊,而是沉默又果决的行动。
而这,也是《苦尽柑来》的母系美学——它从不高举空洞的理念,而是用一地鸡毛的生活经验,织就一张张细密而温柔的网。以乐生的日常哲学,消解宏大叙事。就像当济州岛社长为了给奥运火炬开路,强拆路边的鱼档时,海女们那句脱口而出的——秋刀鱼当然比奥运会更重要。
活生生的人,当然比冰冷的结构更重要。
落实的照料,当然比空口白牙的承诺更重要。
自主经营的感情,当然比天生的血缘更重要。
一个人真实的人生体验,比任何虚妄的理念都重要。
#
从女孩到女人,
女性的精神成长
从未离家
所以其实,看《苦尽柑来》时,我们一直在想,拥有母系家族叙事的女孩,也许幸运就幸运在,无论她们的人生成功与否,都可以从根本性地避开,那个专属于女性的命运咒语——“女孩长大了就没有家。”很多女性成长,几乎都要“经过”这样一种失落感。成年之后,她们就不得不与原生家庭逐步割席。嫁入另一个家庭也好,独立漂泊也罢。现实要么逼迫她们离开熟悉的家,走进一个新的、陌生的空间,去适应一个不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家庭的秩序。要么就是以天为被、以地为席,像蒲公英一样在广阔的远方独立驻扎、野蛮生长。因此,这个时代的很多女孩,为了不丢失自己,大多数都选择了后者。出走,似乎成为现行条件下,无奈却也最有益身心和发展的选择。但发展母系家族叙事,却让我们看到除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图景。
女孩,也可以拥有寻根的权利。
女孩,不必非得在流浪和做客中二选一。
女孩,也可以拥有一种稳固而持续的主人感。
就像爱纯。你会发现,在精神上,她从未离家。母亲光礼,是她永远的内在坐标。而最终,哪怕波折坎坷,她还是在同一个房子里,从女儿长成了母亲。那个母亲光礼一直努力想攒钱买下,却一直存不够钱买的房子,终于在爱纯和宽植这一辈的努力下,正式成为了她们家的房产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,爱纯就是光礼生命的延续和扩容。爱纯在生活里的继续挣扎,让光礼短暂的生命无法变现的执念,终于开花结果。所以光礼甚至会在爱纯的梦里,跑过来擦地。旧旧的木质老房,容纳的,不仅有光礼一辈子的不甘和努力。更是爱纯最初的人生体验。房子里挂着光礼的照片,挂着爱纯写给母亲的“笨鲍鱼”诗句,成了屋子最温柔的注脚。这是爱纯的少女时代,也是她家庭记忆的起点。
爱纯的小家,不是她“另起炉灶”的成果,而是她和母亲共同打造的家屋,在时间长河中自然过渡出的延绵与继承。在那个房子,后来慢慢多了女儿金明的三轮车、贝壳衣柜,还有属于下一代的笑声与气味。后来为了凑金明留学的费用,爱纯做主卖掉了老房子,却是带着满满的家族记忆搬到了新址。而到最后,创业成功的金明,又把承载了三代女性回忆的老房子买了回来。爱纯从未失家,而一直是这个家的主人。她的成长,是一种绵延——不是“嫁出去”,不是“出走”,不是“离开”,而是留下、扎根、继续爱,继续伸展。
拥有母系家族叙事的女孩,不必再挣扎着找归属。她们一出生,便被允许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位置。她们可以在婚姻中、职场中摸索伸展,但却没了必须在这些地方得到“容身之所”的恐惧和焦虑,因为母亲,已经为她们建好了“可以回来的地方”。就像《俗女养成记》的女主陈嘉玲。40岁,狼狈失意,却仍能回家。
我们曾经赞过她幸运,如今又终于领悟,那不只是因为她个体的幸运,而是她的家庭中,同样有一份母系智慧在悄悄流动。当她从台北的光鲜职场辞职回家,小心翼翼地走进厨房,问妈妈会不会失望,向来好强努力、对世俗成就有执念的母亲,却只是心疼地说——“你开心,我就开心。”她就知道,自己没有被放弃。她依然属于这个家。
“无论多少岁,都会想起妈妈。”这不是幼稚,而是一种被爱过的证据。那说明你从未和原生家庭、和母亲、和那条母系传承的血脉真正割裂。
就像爱纯,无论10岁、20岁,还是70岁。
她一直都在看向妈妈。
始终怀念,始终眷恋,始终愿意——
为那份源自母亲的温柔力量,写下一首又一首“笨鲍鱼”的诗。
文/香芹又青了
*图片源于网络
©版权声明:时尚芭莎网编辑时尚芭莎,本文系时尚芭莎网独家原创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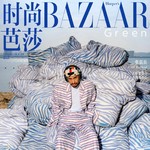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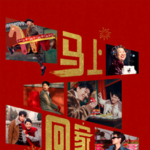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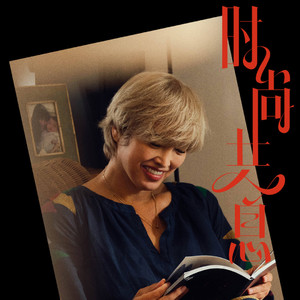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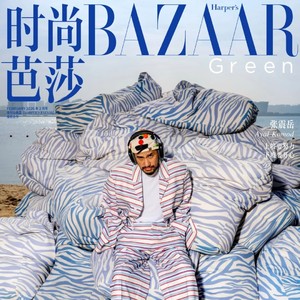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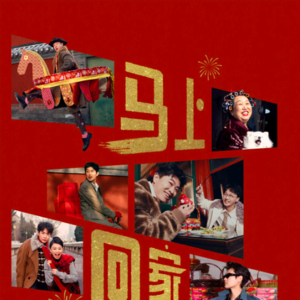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