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时尚芭莎网讯】时尚芭莎
你有没有发现,万圣节变装游行,在全世界都越来越流行了?
最近几年,不仅欧美,在东京、首尔、曼谷、香港乃至中国其他城市,奇装异服的年轻人,在万圣节,自发走上街头,扮演网络热梗、热门角色、社会名人,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大型cosplay狂欢现场。
而且,其热度逐年上升,东京、首尔的街头甚至一度因为过度狂热,引发骚乱。每年这一天,警察都得严阵以待!
各地年轻人,现如今,都快要把万圣节这个西方传统“鬼节”,改造成“万梗节”了。神秘、恐怖的氛围不断减弱,扮演鬼怪的人也越来越少,反而是网络热梗在街头乱飞。
那么,问题来了!
· 万圣节变装游行的热度为何在逐年升高?
·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在街头“装疯卖傻”?
· 它是如何快速传播演变成一场全球狂欢的?
今天,我们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拆解这场“节日狂欢”的背后逻辑——它如何与消费主义、全球化以及新部落主义化纠缠在一起?
这场看似“胡闹”的集体释放与身份表演的派对,为何是宣告社会进入全新时代的标志?
法国社会学家马费索利认为,人类社会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——新部落主义时代!
那么,什么是新部落主义时代呢?
他认为,今天的年轻人,越来越不再依附于家庭、宗族、村落、民族等固定身份,而是走向短暂的、匿名性的、可选择性的“情感部落”,他们以兴趣、爱好、消费认同为名目聚在一起。前工业社会中,感性的象征性的仪式性的共同体部落精神在当下社会正在回归。
万圣节变装游行就很好地符合了这种新部落主义时代的特征,它是无组织的自发行动,是人们在享受氛围,共享情感的一种集体欢腾!
《星期三》
这种新部落主义精神又为何出现复兴了呢?
这种节日狂欢其实是失落了一段时间的民间行动!在古代很常见!
俄罗斯文艺评论家巴赫金就描述过,在中世纪欧洲,每到愚人节、丰收节期间,人们戴上面具,装扮成鬼神,用粗俗、戏谑、夸张的语言和身体表演,上演对各种宗教和世俗权威的戏仿和嘲笑,人们暂时推翻日常秩序,释放被压抑的欲望和生命力。那是一个人人参与的“反日常的节日世界”。
在中国古代也一样。庙会、灯会等各种节日里,民众也是戴着各种面具,装扮成鬼、神、灵兽游行,在笑与闹中共同体验集体欢腾与生命的狂欢。
在巴赫金看来,这种节日狂欢是一种“短暂的解放”,人们暂时摆脱社会等级、身份区隔,打破日常的严肃和礼节,以宗教为纽带,在非理性与想象力的海洋里重建和凝聚共同体。
《锦绣芳华》
可是,进入现代社会之后,这种节日狂欢随着现代社会的祛魅化,却逐渐在社会之中衰落了。
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认为,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“祛魅(disenchantment)”。宗教、死后世界、巫术、迷信、非理性、神秘主义等都被社会有组织地剔除出去,被经济合理性、世俗内禁欲、计算、效率、规则、契约、结构、秩序所取代。
现代社会是极端面向现世的,拒绝谈论任何超验的事物,敌视非理性。一方面,社会变得井然有序。但是,那种象征性的、情感性的集体狂欢精神却一步一步弱化下来了。
然而,当下社会中的万圣节变装游行,却又开始复活前工业时代的节日狂欢。
它是一个大众自发参与的,无论阶层、民族、性别、性取向,所有人在装扮一番之后,暂时解除身份区隔,短暂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秩序,他们借助节日,通过角色扮演、网络文化,表达戏谑与戏仿,在有限的时间里,享受一种瞬时的、活在当下的、游牧式的狂欢!整个过程是象征性的感性的,而不是肃穆的理性的,人们仿佛正在重新召唤失落已久的“部落精神”。
《黑白魔女库伊拉》
这种复兴,被马费索利称作——社会的再魅化。那么,当下社会,为什么重新“再魅化”了呢?
如果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,“再魅化”在社会的各种角落之中都有所体现。如最近在发达国家,各色新兴“宗教”不断出现,神秘主义、占卜、心灵疗愈重新复兴。其实,万圣节变装游行和这些社会变化,是同一个再魅化趋势的一部分。
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就是在“贩卖”一种世界观。这种“世界观贩卖”,其实也流行于日常文艺消费之中。如漫威电影宇宙、哈利·波特、赛博朋克、日本动漫……这些作品,越来越不再满足于讲一个故事,而是在构筑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系统。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“可以居住的宇宙”,让人沉浸其中。
日本动漫就是其典型。日本学者大塚英志在《物语消费论》中就指出,从20世纪70、80年代开始,日本出现了大量“御宅族”。
所谓御宅族的特点是,他们比起现实生活,更热衷于虚拟世界,试图在现实中复刻动漫生活方式:玩各种cosplay、收集昂贵的动漫手办、沉溺于同人创作、游荡于动漫主题餐厅、谈二次元恋爱。他们不只是消费角色,而且是在消费一种完整的意义体系——一种可替代现实的“世界观”。
《银魂》
那么,为什么出现这种消费世界观现象了呢?这又是如何和我们今天要讲解的万圣节变装游行产生了联系呢?
在很多研究者看来,这种再魅化是二战之后,宏大叙事的弱化,导致人们从虚拟叙事中寻求意义的结果。所谓宏大叙事,就是国家、民族、宗教这种能为人生提供统一意义的叙事框架。它告诉你“为什么活着”“要为谁奋斗”。
在一战、二战之前,尤其是日本、德国,人们深信民族主义、信仰国家神话。社会高度组织化,个人被纳入庞大的集体机器中,人们统一在同一个宏大目标之下,热衷于迈向民族共同体的复兴。这个时候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、结构化的,这样的社会虽然压抑,人们却可以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里,寻求得到生活的意义。
但一战、二战的惨剧,让人们彻底怀疑这种叙事。于是,旧的国家神话崩塌了。紧接着,战后六七十年代,左翼革命成为新的信仰。学生运动、反战运动、平权运动此起彼伏,年轻人试图在“乌托邦革命”中重建意义。但当冷战对立弱化、理想破碎之后,信仰再次坍塌。
《银魂》
接下来发生的事,就非常戏剧化了。从80年代开始,一些国家原本激进的左翼革命者们,竟然纷纷转向了宗教与灵修。比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,它的核心成员来自左翼学生团体。日本赤军解体后,也有人投入冥想与灵性修行。在美国,新左派运动也演变成“新灵性运动”,反越战的嬉皮士们纷纷转向冥想、瑜伽、生态灵性。在拉美出现了解放神学,在欧洲出现了“灵性左翼”。看似完全对立的“灵修”与“革命”,居然在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奇怪的联姻。
为什么呢?明白这里的逻辑,就可以查清楚万圣节变装游行兴起的源头。
因为左翼革命其实是宏大叙事的终结者。他们批判国家神话、宗教意识形态,提出“所有宏大叙事都是幻象”。他们要打碎一切统摄性的意义系统,让每个人自由、多元、差异化。今天的所谓白左,就是抱有这种理念的人的残留。
但结果是——当宏大叙事被打碎,人类的意义感也被打碎了。没有了共同的信仰,人就只能回到个体内心,去寻找意义。于是,灵性、新宗教、神秘主义、动漫世界观、阴谋论、心灵疗愈……全都成了人们逃离虚无、重建意义的方式。他们在消费故事、理想、叙事、信仰、意义与世界观。他们在一个又一个“虚拟部落”里,重建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
《老友记》
那么,为什么现在的万圣节,大家越来越少扮鬼,而是越来越热衷于扮“梗”?
原因其实不在节日本身,而在整个时代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影像与叙事包围的世界。年轻人每天睁眼看到的,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,而是各种屏幕、短视频、综艺、电影、动画......。我们的笑点、情绪、想象,早就不是从现实生活里来的,而是从这些“虚拟世界”中提炼出来的。这些虚拟文艺作品,已经开始变得“比真实生活还要真实”,被鲍德里亚称作“超真实社会”。
连“新闻”都开始故事化、梗图化、表情包化,虚拟影响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意义来源。甚至很多人开始喊:“我现在活着的最大动力,就是等下一集更新。”这句话不是玩笑,而是整个时代的写照。
所以,当年轻人cos各种网络梗、影视角色、综艺人物时,其实他们在做的,不只是搞笑。他们是在通过“扮演”,把自己接入一个虚拟世界观。这和御宅族玩cos、写同人、沉迷二次元,其实是一回事——都是在用虚拟文艺的叙事中,重建意义的结果。
所以,我们总结一下。
古代的万圣节,是宗教世界观的产物。前工业时代的人,给他们创造了活着的意义的是宗教。所以他们通过模仿鬼魂、神明,是要和宗教所虚构出来的死后的或者来世的世界进行连接。这个时代的萨满巫师们,通过舞蹈、幻觉、通灵,进入神话性的仪式空间。
而到了现代社会,宗教的力量衰落,社会开始祛魅化,造就死后世界支撑现实世界的意义结构遭遇了崩塌。人们把生活的意义,开始投注在现实里,或者更确切地说,投注在未来可实现的乌托邦理想里。各种主义、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,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这些意识形态有着同样的主张,社会要走向进步,在现实世界里,构建理想的乌托邦。
但是,谁也没有想到,社会的后现代化开始了。
发达国家的年轻人,开始冷漠于现实的政治、革命、乌托邦。他们觉得这些宏大叙事都是骗人的。于是,他们开始转向内心世界,纷纷开始投入进各种灵性叙事、虚拟世界观、消费认同之中。这时候,意义不再从“现实”中来,而是从“故事”中来。
所以,现在的万圣节,年轻人cos网络热梗、动漫角色。他们不是在连接死后世界,而是在接入一个又一个虚拟叙事系统。这和古代人扮鬼神的逻辑,其实完全一样。
古代节日——和神话、宗教、鬼神、死亡有关。比如中国的清明、中元、端午,欧洲的诸圣节等,这些节日让人连接“宗教性的世界”。
而现代社会的节日,和意识形态、国家、革命有关。如美国的独立日、奴隶解放日、劳动节、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等,这些节日让人连接“现世的乌托邦”。
《九重紫》
但今天的年轻人,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消费节、动漫节、购物节、粉丝节。节日的主办方不再是神庙或国家,而是企业与兴趣社群。人们普遍是在和“虚构叙事”进行连接。万圣节等传统节日,也都在明显地呈现出商业化、爱好团体化的趋势。
所以,在原始部落社会里,人们的服装是表征部落身份的。而在农业时代,服装有着严格的等级和身份限制,你是哪一个身份穿哪一种服装。宏大叙事时代,人们是以特定价值观为一体穿着特定服装,如代表民族的服装、代表革命的服装等等。而后现代化的消费主义时代,人们的服装愈来愈穿越了上下身份和民族,造成世界各地服装变成了展现认同、爱好、价值观、生活方式的工具。
漫威粉丝穿着漫威周边服装,偶像歌手粉丝穿着应援偶像歌手的服装,足球迷穿着喜欢的队服......我们通过装扮,在身份流动的社会中,表征自己,连接进入虚拟叙事意义的系统。
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崛起》
于是,我们会发现——在“叙事消费”崛起的今天,社会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“再魅化”。
不过,这种社会的再魅化和前工业时代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。前工业时代的节日狂欢是在宗族、部落这种稳定共同体里展开的:祭祖是为了凝聚血缘,祭土地神是为了稳固村落。每个节日,都是在说:“我们是谁,我们属于谁。”
但,现在的万圣节呢?是已经匿名化了的个体之间,流动的身份认同之下,没有组织性的自发爆发的狂欢。
当下社会中的人,越来越讨厌固定的身份,不断拥抱流动性的身份。民族的、宗族的、地缘的、血缘的身份都开始弱化,甚至连性别都在变得可选择。在这种流动性的多元身份社会之中,节日不再是为了凝聚共同体,而是为了体验一种瞬时的、匿名的、无目的的快乐。
这和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的性情无比契合。互联网本身的匿名机制,让阶层、民族、性别等传统身份都开始隐匿了。
而万圣节恰是通过变装,通过第二层皮肤的装饰,就体现了这种互联网时代的匿名狂欢的气氛。
《老友记》
而且,这种瞬时的狂欢,也符合后宏大叙事时代,时空观念的重构趋势。
宏大叙事,主要回答“我是谁、我从哪里来、我要走向哪里”的意义建构问题。这些叙事之中,存在着落后的过去,要进步下去的未来的一个线性时间观。
社会进步观占据主流,事实上是宏大叙事时代中,随着社会的祛魅,人们把自己的希望,寄托在现实世界中的未来乌托邦的结果。
但如今,宏大叙事的解体,让这种线性时间观出现了又一次重组。人们不再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而压抑自己,人们越来越强调一种即时的消费、享乐、狂欢。于是,“理性计划型的人”变成了“及时行乐型的年轻人”。勤勤恳恳在工厂的劳动者,转换成了提前消费、热衷娱乐的玩家。
理性规划是要以未来回报为前提的,但是未来的崩塌,导致合理性规划再也无法压抑非理性狂欢。“狂欢节”这种步入共在时的喜悦的情感的节日,开始重新回归我们的视线。
同时,我们的空间观,也在被彻底重构了。全球化和媒体技术的发展,让我们进入了一种“同步的共在时空”。
中国和欧洲距离遥远,古代社会不得不形成不同文化。而当下社会,距离已经不再是文化交流的强力阻碍。你会发现,巴黎、东京、纽约、上海的特定空间之中,相似的cosplay活动可以在同一天举行。流行文化的传播几乎是瞬时的,全球的年轻人可以做到同一秒刷到同一个梗,同一天装扮同一个角色。
空间,不再是用距离来划分的。城市开始马赛克化:一个街区里既有美式咖啡馆,也有二次元主题店,还有非洲手工艺小摊。
《星期三》
不同文化不再隔绝,而是拼贴在一起。这导致20世纪后半期拼贴艺术的崛起。事实上,我们的生活,恰是一幅文化拼贴画——客厅里可能摆着非洲的木雕、欧洲的香水、日本的刀剑。
而万圣节变装狂欢,正是这种拼贴文化的极致体现。它把不同国家、不同亚文化、不同媒介角色,全都糅在一起。cos的不只是鬼怪,而是全球流行文化的混合体。
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日常——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“异文化拼贴式的生活”,甚至会像游客一样,去体验不同亚文化群体的存在方式。
《老友记》
这种全球同步的节日狂欢,正是媒体技术带来的“时空脱域”的结果。网络让我们从地理空间中抽离,所有人被拉进一个统一的虚拟全球时空。
身份不再稳定,地域不再重要,新的连接,发生在爱好、情感、氛围之中。
也正因如此,文化的传播速度,达到了“病毒”级别。万圣节变装游行,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京、香港、首尔萌芽,到近几年,几乎像“病毒”一样蔓延整个亚洲都市圈。
归根到底,这种传播击中了,生活在宏大叙事解体,高度城市化全球化,媒体技术异常发达的,后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的内心。
当下的年轻人显然已经普遍厌倦后宏大叙事时代中原子化的孤独,也厌倦宏大叙事带来的组织化的生活。
情感的、融合的、群居性的,以情绪、感受、氛围为纽带的自发性新部落开始出现全面复兴。新部落主义时代中,人们不再靠理念连接,而是靠感觉、靠氛围、靠共振,通过共享虚拟意义系统进行连接。人们由多元微观文化网络所统摄,开始出现从理性秩序到感性秩序的社会转型。
这仿佛是对理性的、进步的、秩序的、宏大叙事所包围的启蒙运动理想的一种颠覆,也是大家更加遵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一种信号。
参考文献:
巴赫金《拉伯雷与他的世界》
涂尔干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
韦伯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
马费索利《部落时代》
罗伯逊《全球化: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》
大塚英志《物语消费论》
大泽真幸《不可能性的时代》
吉登斯《现代性的后果》
鲍德里亚《象征交换与死亡》
东浩纪《动物化的后现代》
©版权声明:时尚芭莎网编辑时尚芭莎,本文系时尚芭莎网独家原创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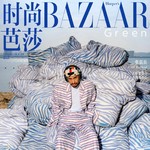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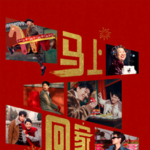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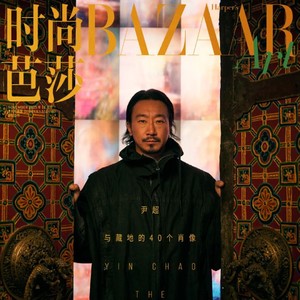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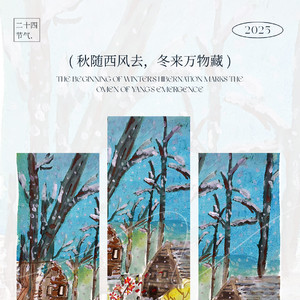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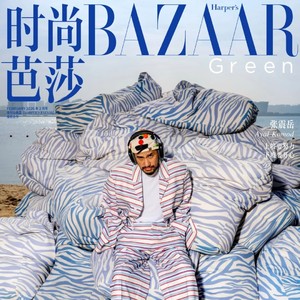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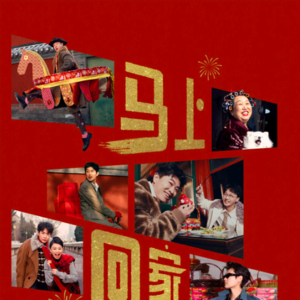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
